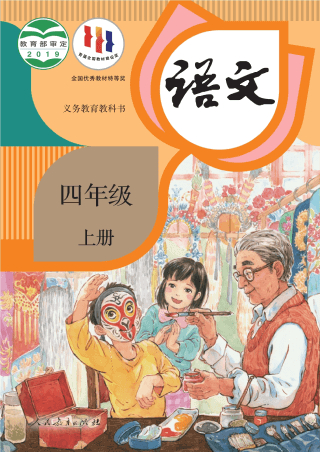在我的故乡,陀螺不叫陀螺,叫作“冰尜儿”,顾名思义,就是冰上的小家伙。
做冰尜儿用的是木头,柳木、榆木、松木、枣木、梨木都可以。抽打冰尜儿,当然是在冬季的冰天雪地里,最好的场所是冰面。好的冰尜儿尖部嵌一颗滚珠,转起来能增加许多妩媚。顶不济的,也要钉上一枚铁钉,否则转不了多少圈,尖部就会开裂。无论嵌上滚珠,还是钉上铁钉,冰尜儿都不会裂开,能毫无怨言地让你抽打,在冰面上旋转,舞蹈。
抽冰尜儿的小伙伴们,都爱比个高下。他们往往各站一角,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尜儿,让它朝对方撞去。这时你看吧,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,旋风般撞向对手,刚一接触,又各自闪向一边,然后重整旗鼓再战——直到其中一方被撞翻才告一段落。赛陀螺每次都是体重个大的一方占上风。因此,只有小陀螺的大多在自家院子里玩,不拿到马路上去应战。况且小陀螺有个难听的绰号叫“角锥”,意思是小且细。抽打“角锥”的大多是拖鼻涕穿开裆裤的,他们的兴趣在于抽鞭子,对陀螺的质量往往不在意。
我从小就不甘人后,更不愿自己的陀螺像金兵见到岳家军,一战即败。于是四处寻找木头,为削出得心应手的陀螺,就差没把椅子腿拿来“废物利用”了。为此不知挨了多少责骂,可仍然不肯住手。然而一个孩子无论如何是削不出高质量的陀螺的,因此,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世界堆满乌云,快乐像过冬的燕子一般,飞到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了。
这种懊恼终于引起了长辈的注意。我的叔叔,一位很有童心的年轻民警,答应在我生日那天送我一只陀螺。这消息曾使我一整天处于恍惚的状态,老想象着那只陀螺英武的风姿。
叔叔的礼物不错!
这只陀螺不是人工削出来的,而是一位木工在旋床上旋出来的,圆且光滑,如同一枚鸭蛋。虽然它远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漂亮,但我极高兴地接受了它。尤其当我看到这枚“鸭蛋”的下端已嵌上一粒大滚珠时,更是手舞足蹈,恨不得马上在马路上一显身手!
我的陀螺刚一露面,就招来了一顿嘲笑。的确,在各色帅气的陀螺面前,它长得不伦不类,该平的地方不平,该尖的地方不尖,看不出一丝一毫与同伴相斗的能力。这使我士气大减,只是在一旁抽打,不敢向任何人挑战。
然而世间许多事都是不可预料的,追求“和平”只是我的个人愿望,小伙伴们不甘寂寞,一个大陀螺的主人开始傲慢地向我挑衅。大陀螺摇头晃脑,挺着肚皮一次次冲过来,我的“鸭蛋”则不动声色地闪躲。一次次冲击,一次次闪躲,终于无法避开,它们狠狠地撞上了!
奇怪的是,我的陀螺个头小,却顽强得出奇!明明被撞翻在一边,一扭身又照样旋转起来。它圆头圆脑,好像上下左右都能找到支撑点似的。结果呢,大陀螺在这个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对手面前,彻底溃败了。
这真是个辉煌的时刻!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,品到了幸运的甜头。无意中获得的“荣誉”,虽然小如微尘,对好胜的孩子来说,也足以陶醉许久了——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,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!
我的冰尜儿,木工随便旋出的小木头块,丑小鸭生出的一只丑鸭蛋,在童年的一个冬日里,给了我极大的欢乐和由衷的自豪。
这真应了一句古话: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。